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526145396528563
我看的「玉想」有李霖燦老師在一九九○年寫的序,序寫完,李老師故去,我重讀「玉想」,想到的是李老師最後一次到東海建築系評圖,忽然打電話找到我,說要來我美術系辦公室坐坐。
我的辦公室是東海舊圖書館晒書後廢棄的空間,沒有人要用。我喜歡它兩邊透光通風,早午都有陽光,掛了竹山民間製作的細竹簾,光線篩過竹簾空隙,就如一卷靜靜的萱紙,戶外樹影雲影都可以在上面留痕跡。
李老師坐定,環看地上陽光,陽光中樹影雲影風光搖曳,忽然轉頭跟我說:「蔣勳,我們都是命好的人,一輩子都在看美好的東西。」
二○○九年初春,重讀「玉想」,想到李老師說的「命好」,想到同樣「命好」的一些朋友,想為老師奠一尊酒,窗外雲嵐變滅,潮起潮落,可以珍惜的還是朋友寄來的春茶在舌口上留著的一段餘甘。
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於八里
人物故事:《故宮 書法 莊嚴》,翁萬戈《陳洪綬的藝術》,《紅色》、楊英風: 有鳳來儀 東海師長: 漢寶德 ; 東海蔣勳《來日方長》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1433714927411671
內容簡介
《玉想》是曉風最成熟的深思,在安靜分析中有激情,在冷眼凝視中有摯愛。她認為經學、史學和哲學可以是一個民族強健的體魄,但「美」卻是維持命脈的和暢的呼吸,本書便是她對美的獻禮。
增訂新版中,除美學大師蔣勳特別為序推薦外,版面重新彩色編排,珍貴圖片與曉風雋永優美的文字相映襯,值得細細品讀。
本書特色
★ 獲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張曉風最受人喜愛的美學散文,美學家欣賞讚譽!
作者簡介
張曉風
江蘇銅山人。得過吳三連、中山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當選過十大傑出女青年,曾任教東吳大學、陽明大學,現為「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副召集人。她編、寫戲劇、雜文、散文。然而真正呈現她面貌的,應是她的散文,可用學者的深度細讀,因它那麼深刻;您可以用孩童的天真翻她的散文,因它是那麼淺明。詩人□弦則稱她是「詩人散文家」。著有散文集《玉想》、《從你美麗的流域》,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小說教室》等。
目錄
〔增訂版〕序
重讀曉風《玉想》,兼懷李霖燦老師∕蔣 勳 002
寫下來,真好(自序) 008
〔初版〕序 序∕李霖燦 016
給我一個解釋(代自序) 022
第一輯 玉 想 玉 想 034
色 識 050
初 心 068 溯
洄 074
火中取蓮 092
故事行 104
天 門 116
仗美執言 132
我彷彿看見 138
會過日子的女人 148
衣宮半日記 154
訪香港導演方育平 162
第二輯 低眉處 值得歡喜讚歎的《歡喜讚歎》 168
中國的眼波 180
以人為鈐記 182
低眉處 184
錯 誤 190
評 語 196
第三輯 有 願 也算攔輿告狀 200
如果你錯了和如果我錯了 208
局長,請聽我說一個觀念 210
冠 禮 216 遊園驚夢 218
有 願 222 河飛記 224
寫於「和氏璧」演出之前 228
老師,這樣,可以嗎? 230
〔新增文章〕 安全的冒險 234
炎方的救贖 238
楊貴妃和她的詩 250
跋 256
序
寫下來,真好
(1)
咦?他是誰?他怎麼會出現在我家門口的公園??他是真的嗎?
是晴暖的禮拜天早晨,我作完禮拜回家,刻意早一點下車,打算穿過這個長著二十棵樹的小公園,並且姑且算它是一趟森林之旅。
然而,我竟遇見他,他似乎正在喝水龍頭流出來的積水,他不動,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或者只是一個塑像?我走近,坐在一張長椅上,定睛看他。他是一隻大約四十公分的鳥,我看到他的頸綬在風中飄動,但我仍不敢相信他是真的,這年頭假東西都做得很像呢!
但我又不忍心驚動他,如果他是真的,他當然該有他不被打擾的權利。於是我坐著,定定的看他。
終於,他轉了一下頭,我才知道他是真的!在地球的某一經緯度上,我曾買下我家住宅,公園在我家門口,我在這個空間上生活了四十年的時間。然而,公園?一向只有從人家家裡逃出來的鴿子,還有麻雀和綠繡眼,偶而有白頭翁,至於這種大型鳥,比鷺鷥還肥大的鳥,我是從來也沒見過呀!
確定他是一隻真鳥以後,我又看了他二個小時,他沒有動作,我也沒有,我只驚奇,他是誰?他怎麼會忽然現身此地,這事得去問劉克襄,反正我一切有關鳥的事都去跟他打聽。二天後我找到劉克襄,並給他看照片:
「哎呀!他是黑冠麻鷺啦!」行家是不用看第二眼的,「最近他也出現在大安森林公園?,不料連你家門口的小公園?也有他們的蹤跡。」
哦,原來他是黑冠麻鷺。
「你記得嗎?十幾年前了,」劉克襄又接著說,「那時候有人想把大安森林公園弄成運動場地,你寫文章反對,後來還是維持了原議。而現在,台北市居然就有了黑冠麻鷺了,你看,這是你爭取來的呀!」
什麼?這隻鳥的出現原來和我也有那麼一點關係,原來他有今日的一枝之棲也跟我當年力爭有關?這件事我已忘了,連那篇文章去了那?都不記得了。可是,卻有一隻黑冠麻鷺來報訊,來跟我打個招呼。大安森林公園離我家不遠,他可能住在那?,偶然飛過街來看看。
真是謝謝克襄,我自己都忘了的事,身為編輯,他卻是有記憶的。我原來只想問他一隻鳥的名字,他卻告訴我更多,他要說而沒說的是:
「嗨!你知道嗎?寫下來,這件事很好喔!寫下來,表達了,成功了,十幾二十年後,你會看到績效!」
(2)
順著克襄的話,我想起不久前專欄作家協會去桃園參觀,車過某地,負責招待我們的東年忽然請車開慢一點,他說:
「你們看,這是桃園神社,是日本時代的木結構建築。當年要拆,是曉風老師寫文章罵了才救下來的,現在,卻是我們重要的觀光景點了。」
我當時也嚇了一跳,民國七十四年,我用可叵筆名寫了一篇「也算攔輿告狀」給當時的徐縣長,這事居然也就蒙天之幸把房子救下來了,民國七十年前後,高信疆所主持的時報人間版大力鼓吹報導文學,附帶的,抗議文學也就跟進了,抗議而能成功,二十年後就一切見真章。
(3)
「寫下來」的好處還不止這些,例如我寫過孫超的陶藝,當時也很想寫他的妻子關正,但時機稍縱即逝。如今關正已走了二年了,患類風濕關節炎的她是怎樣苦撐苦熬才努力扮演了賢妻的角色,那真該是一篇字字含淚的文章,可惜已經沒有機會了。
相較之下,我寫了林淵,他雖已走,但我較少憾恨,覺得他和他的作品,都長長的活在那?。在石雕?,也在文字?。
(4)
「你只能寫抒情文。」
我的中學老師如此告訴我,我也深深相信。
我漸漸才知道我錯了,十幾歲的我並不是不會寫說理文,而是我那時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麼理,心中沒有什麼道理的孩子那?說得出理來呢?但等我把自己整理好,居然年已四十了。
《玉想》這本書是我中年之際寫的,也必須到這個年紀才能說出對玉石的想法,對彩色的見解,我把道理說出來了,我很高興自己做了這件事,寫下來,真好。
(5)
經過十九年,九歌打算把《玉想》這本書重新付梓。我在重校舊稿時,心中充滿感恩和喜悅。唯一的悲傷是當年作序的李霖燦老師這一次來不及看見了,他於一九九九年病逝美國。啊!算起來也是十年前的事了。
記得有一次我開車載李老師和胡品清老師去陽明山二子坪走走,老師非常高興,後來還好幾次打電話來說:
「真是個好地方啊,沒想到這麼鄰近之處,(老師住外雙溪故宮的宿舍)也有這麼一處有意思的地方啊!」
老師是見過大山大水的人,實際世界?的大山大水,以及畫紙上的明山秀水,他一再謝我二子坪之遊其實也只是對後生的仁慈,我能「被他所寫」,也真是幸運。
(6)
新版《玉想》,又增加了三篇文章,是為《長生殿》、《牡丹亭》以及國光「鬼.瘋系列」演出而寫的。能為國劇作些詮釋原來並不在我的人生規劃?,但人生又那?是我們所能一手擘劃的呢?
(7)
總之,能寫下來,真好。至於它是瓊漿,還是糟醨,也就交給時間去辨嚐吧!
張曉風 九八年三月
〈如果算陰曆,就是己丑年如月。如月,就是二月的意思,指的是它繼承了那份蓬勃,並使之更為一逕前推,真是個有美感的月份。)
推薦序
重讀曉風《玉想》,兼懷李霖燦老師 蔣 勳
初春重讀「玉想」,想到李老師說的「命好」,想到同樣「命好」的一些朋友,想為老師奠一尊酒,窗外雲嵐變滅,潮起潮落,可以珍惜的還是朋友寄來的春茶在舌口上留著的一段餘甘。
張曉風的「玉想」要重新出版了,我把這一冊大多寫於上一世紀八○年代的散文拿在手中重新讀了一次。
讀著讀著,覺得午后河邊乍明乍滅的陽光真好,隔著河,對面的大屯山一帶白雲卷舒,或來或去,配合著時起時落的潮聲,我就放下了書,跑去找台南朋友新寄來的今年剛收的春茶。
「玉想」是要有一盞「春茶」搭配著讀的。
這些近三十年前都讀過的文字,在春茶的新新的喜氣得意的滋味裡,一一在沸水中復活了。
曉風寫這一系列文字的時候我們常一起出去玩,有一個「花酒黨」這樣的名字,五六個人,七八個人,帶一盅酒,聽聞什麼地方有好花,好山水,便一路殺去,盤旋數日。
我跟曉風、慕蓉去過南仁山,中央山脈到尾端的餘脈,低矮丘陵起伏,很像黃公望八十二歲的名作「富春山居」。那時候兩派學者正為了故宮兩卷「富春山居」孰真孰假鬧得不可開交。從乾隆皇帝開始就鬧不休的「雙胞案」,到了山水面前,忽然想起黃公望在「無用卷」卷末寫的「巧取豪奪」四個字。也許黃公望一生賣卜為生,到了八十二歲真的卜算出了這張畫要到人間去經歷一段「巧取豪奪」的滄桑罷。
被稱為「元四家之首」的黃公望,八十二歲的名作,不再只是「名作」,而是一堆「巧取豪奪」的「慾望」。在不同的人手中流轉,有人為這張畫傾家蕩產,有人為這張畫死時不能瞑目,吳洪裕因此要姪子燒起火來燒畫殉葬,卻沒想到煙火騰騰,畫燒成了兩段,死者瞑目了,活著的人還是從火堆中搶出,前段成為「剩山圖」,歷經大收藏家吳湖帆的手,最後進入了浙江博物館。後段腳長一段也歷經不同人收藏,最後入了清宮,被乾隆當成假畫,1949年隨故宮南遷,到了台灣。
做學生的時候,有幸運隨莊嚴老師、李霖燦老師一起看畫,拿出一卷「富春山居」,四、五個研究生,一面跟老師聊天,一面努力做筆記。
我是不用功的一個,不知道為什麼總惦記著元代一張紙上什麼地方無意間滴下一水痕,或汗,或淚,或是某一春日不經意的雨滴,留在上面,沒有人覺查,水痕宛轉,卻隨歲月成為滄桑的斑剝,那就是大書家所說的「屋漏痕」嗎?
我也惦記著畫上在明末清初留下的煙火記憶,在灰燼的邊緣,一點點驚恐險絕的遺跡。
曉風像是在談「玉」,談「陶瓷」,談中國藝術中的顏色,談刺繡,其實,也許我們有一樣的毛病,談著談著,會情不自禁,跑去專心凝視一塊玉上的「瑕疵」。曉風說的「瑕疵」,是書畫裡的「屋漏痕」,是玩古玉的人津津樂道的「沁」。因為入了土,那玉和石灰,松脂,人的骨血,動物的腐屍依靠在一起,年月久了,玉石上就有一塊去除不了的「斑」,或赭或灰,或如髮絲,或如血脈,或如淚痕,丹心要化為碧,便是「沁」這個字,「沁」是如此深的記憶,「沁」入肺腑,是對抗歲月,對抗毀滅的驚叫。
中國的美學,要看到黃公望「巧取豪奪」之外的歲月的痕跡,才會有帶著淚痕的驚叫。
那時候在「富春山居」長卷前面,李霖燦老師沒有說什麼話,他似乎對爭辯筆仗都不感興趣,他談中國藝術的文字像詩,不像論文。
這個原來杭州藝專出身要做畫家的學者,因為戰爭,誤打誤撞走了西南邊陲的大山,遇到沈從文,知道生命裡有許多意外,像曉風在「玉想」中說的「錯誤」,李老師和南遷的故宮書畫註定要走在一起,走到台灣,註定要在他的凝視下,看到一千年前藏在「谿山行旅圖」樹叢中「范寬」這兩個字,找到目前全世界唯一可以確定的「范寬」的真蹟。
我帶學生到故宮看「谿山行旅」,指給他們看樹叢中隱藏的名字,他們覺得奇怪,「怎麼一千年來都沒有人看得見?」
「問得好!」我心裡想,這個名字是註定要在一千年後在台灣由李霖燦看到的,就像「沁」這個字,必得要有一個「心」字,沒有「心」,玉也只是一塊石頭,纏綿也只是一堆亂絮,陶瓷不過就是土胎而已。
曉風有心,所以有了「玉想」,「玉想」談中國藝術之美,也像詩,不像論文。
我看的「玉想」有李霖燦老師在一九九○年寫的序,序寫完,李老師故去,我重讀「玉想」,想到的是李老師最後一次到東海建築系評圖,忽然打電話找到我,說要來我美術系辦公室坐坐。
我的辦公室是東海舊圖書館晒書後廢棄的空間,沒有人要用。我喜歡它兩邊透光通風,早午都有陽光,掛了竹山民間製作的細竹簾,光線篩過竹簾空隙,就如一卷靜靜的萱紙,戶外樹影雲影都可以在上面留痕跡。
李老師坐定,環看地上陽光,陽光中樹影雲影風光搖曳,忽然轉頭跟我說:「蔣勳,我們都是命好的人,一輩子都在看美好的東西。」
二○○九年初春,重讀「玉想」,想到李老師說的「命好」,想到同樣「命好」的一些朋友,想為老師奠一尊酒,窗外雲嵐變滅,潮起潮落,可以珍惜的還是朋友寄來的春茶在舌口上留著的一段餘甘。
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於八里
是許多混沌的生命中忽然脫穎而出的那一點靈光。
一、 只是美麗起來的石頭
一向不喜歡寶石──最近卻悄悄的喜歡了玉。
寶石是西方的產物,一塊鑽石,割成幾千幾百個「割切面」,光線就從那裏面激射而出,挾勢凌厲,美得幾乎具有侵略性,使我不由得不提防起來。我知道自己無法跟它的凶悍逼人相埒,不過至少可以決定「我不喜歡它」。讓它在英女王的皇冠上閃爍,讓它在展覽會上伴以投射燈和響尾蛇(防盜用)展出,我不喜歡,總可以吧!
玉不同,玉是溫柔的,早期的字書解釋玉,也只說:「玉,石之美者。」原來玉也只是石,是許多混沌的生命中忽然脫穎而出的那一點靈光。正如許多孩子在夏夜的庭院裏聽老人講古,忽有一個因洪秀全的故事而興天下之想,遂有了孫中山。又如溪畔群童,人人都看到活潑潑的逆流而上的小魚,卻有一個跌入沈思,想人處天地間,亦如此魚,必須一身逆浪,方能有成,只此一想,便有了蔣中正。所謂偉人,其實只是在遊戲場中忽有所悟的那個孩子。所謂玉,只是在時間的廣場上因自在玩耍竟而得道的石頭。
二、克拉之外
鑽石是有價的,一克拉一克拉的算,像超級市場的豬肉,一塊塊皆有其中規中矩秤出來的標價。
是無價的,根本就沒有可以計值的單位。鑽石像謀職,把學歷經歷乃至成績單上的分數一一開列出來,以便敘位核薪。玉則像愛情,一個女子能贏得多少愛情完全視對方為她著迷的程度,其間並沒有太多法則可循。以撒辛格(諾貝爾獎得主)說:「文學像女人,別人為什麼喜歡她以及為什麼不喜歡她的原因,她自己也不知道。」其實,玉當然也有其客觀標準,它的硬度,它的晶瑩、柔潤、縝密、純全和刻工都可以討論,只是論玉論到最後關頭,竟只剩「喜歡」兩字,而喜歡是無價的,你買的不是克拉的計價而是自己珍重的心情。
三、不須鑲嵌
鑽石不能佩戴,除非經過鑲嵌,鑲嵌當然也是一種藝術,而玉呢?玉也可以鑲嵌,不過卻不免顯得「多此一舉」,玉是可以直接做成戒指、鐲子和簪笄的,至於玉墜、玉珮所需要的也只是一根絲繩的編結,用一段千迴百繞的糾纏盤結來繫住胸前或腰間的那一點沈實,要比金屬性冷冷硬硬的鑲嵌好吧?
不佩戴的玉也是好的,玉可以把玩,可以做小器具,可以做既可卑微的去搔癢,亦可用以象徵富貴吉祥的「如意」,可做用以祀天的璧,亦可做示絕的玦,我想做個玉匠大概比鑽石割切人興奮快樂,玉的世界要大得多繁富得多,玉是既入於生活也出於生活的,玉是名士美人,可以相與出塵,玉亦是柴米夫妻,可以居家過日。
四、生死以之
一個人活著的時候,全世界跟他一起活──但一個人死的時候,誰來陪他一起死呢?
中古世紀有齣質樸簡直的古劇叫「人人」(Every Man),死神找到那位名叫人人的主角,告訴他死期已至,不能寬貸,卻准他結伴同行。人人找「美貌」,「美貌」不肯跟他去,人人找「知識」,「知識」也無意到墓穴裏去相陪,人人找「親情」,「親情」也顧他不得……
世間萬物,只有人類在死亡的時候需要陪葬品吧?其原因也無非由於怕孤寂,活人殉葬太殘忍,連土俑殉葬也有些居心不仁,但死亡又是如此幽闃陌生的一條路,如果待嫁的女子需要「陪嫁」來肯定來繫連她前半生的娘家歲月,則等待遠行的黃泉客何嘗不需要「陪葬」來憑藉來思憶世上的年華呢?
陪葬物裏最纏綿的東西或許便是玉琀蟬了,蟬色半透明,比真實的蟬為薄,向例是含在死者的口中,成為最後的,一句沒有聲音的語言,那句話在說:
「今天,我入土,像蟬的幼蟲一樣,不要悲傷,這不叫死,有一天,生命會復活,會展翅,會如夏日出土的鳴蟬……」
那究竟是生者安慰死者而塞入的一句話?抑是死者安慰生者而含著的一句話?如果那是願心,算不算狂妄的侈願?如果那是謊言,算不算美麗的謊言?我不知道,只知道玉琀蟬那半透明的豆青或土褐色彷彿是由生入死的薄膜,又恍惚是由死返生的符信,但生生死死的事豈是我這樣的凡間女子所能參破的?且在這落雨的下午俯首凝視這枚佩在自己胸前的被烈焰般的紅絲線所穿結的玉琀蟬吧!
我在玉肆中走,忽然看到一塊像蛀木又像土塊的東西,彷彿一張枯澀凝止的悲容,我駐足良久,問道
「這是一種什麼玉?多少錢?」
「你懂不懂玉?」老闆的神色間頗有一種抑制過的傲慢。
「不懂。」
「不懂就不要問!我的玉只賣懂的人。」
我應該生氣應該跟他激辯一場的,但不知為什麼,近年來碰到類似的場面倒寧可笑笑走開。我雖然不喜歡他的態度,但相較而言,我更不喜歡爭辯,尤其痛恨學校裏「奧瑞根式」的辯論比賽,一句一句逼著人追問,簡直不像人類的對話,囂張狂肆到極點。
不懂玉就不該買不該問嗎?世間識貨的又有幾人?孔子一生,也沒把自己那塊美玉成功的推銷出去。《水滸傳》裏的阮小七說:「一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但誰又是熱血的識貨買主?連聖賢的光焰,好漢的熱血也都難以傾銷,幾塊玉又算什麼?不懂玉就不准買玉,不懂人生的人豈不沒有權利活下去了?
當然,玉肆老闆大約也不是什麼壞人,只是一個除了玉的知識找不出其他可以自豪之處的人吧?
然而,這件事真的很遺憾嗎?也不盡然,如果那天我碰到的是個善良的老闆,他可能會為我詳細解說,我可能心念一動便買下那塊玉,只是,果真如此又如何呢?它會成為我的小古玩。但此刻,它是我的一點憾意,一段未圓的夢,一份既未開始當然也就不致結束的情緣。
隔著這許多年如果今天那玉肆的老闆再問我一次是否識玉,我想我仍會回答不懂,懂太難,能疼惜寶重也就夠了。何況能懂就能愛嗎?在競選中互相中傷的政敵其實不是彼此十分了解嗎?當然,如果情緒高昂,我也許會塞給他一張《說文解字》中抄下來的紙條:
玉,石之美者,有五德
潤澤以溫,仁之方也
腮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
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
不撓而折,勇之方也
銳廉而不忮,絜之方也。 然而,對愛玉的人而言,連那一番大聲鏜鞳的理由也是多餘的。愛玉這件事幾乎可以單純到不知不識而只是一團簡簡單單的歡喜。像嬰兒喜歡清風拂面的感覺,是不必先研究氣流風向的。
六、瑕
付錢的時候,小販又重複了一次:
「我賣你這瑪瑙,再便宜不過了。」
我笑笑,沒說話,他以為我不信,又加上一句:
「真的──不過這麼便宜也有個緣故,你猜為什麼?」
「我知道,它有斑點。」本來不想提的,被他一逼,只好說了,免得他一直囉嗦。
「哎呀,原來你看出來了,玉石這種東西有斑點就差了,這串項鍊如果沒有瑕疵,哇,那價錢就不得了啦!」
我取了項鍊,儘快走開。有些話,我只願意在無人處小心的,斷斷續續的,有一搭沒一搭的說給自己聽:
對於這串有斑點的瑪瑙,我怎麼可能看不出來呢?它的斑痕如此清清楚楚。
然而買這樣一串項鍊是出於一個女子小小的俠氣吧,憑什麼要說有斑點的東西不好?水晶裏不是有一種叫「髮晶」的種類嗎?虎有紋,豹有斑,有誰嫌棄過它的皮毛不夠純色?
就算退一步說,把這斑紋算瑕疵,世間能把瑕疵如此坦然相呈的人也不多吧?凡是可以坦然相見的缺點都不該算缺點的。純全完美的東西是神器,可供膜拜。但站在一個女人的觀點來看,男人和孩子之所以可愛,正是由於他們那些一清二楚的無所掩飾的小缺點吧?就連一個人對自己本身的接納和縱容,不也是看準了自己的種種小毛病而一笑置之嗎?
所有的無瑕是一樣的──因為全是百分之百的純潔透明,但瑕疵斑點卻面目各自不同。有的斑痕像蘚苔數點,有的是砂岸逶迤,有的是孤雲獨去,更有的是鐵索橫江,玩味起來,反而令人忻然心喜。想起平生好友,也是如此,如果不能知道一兩件對方的糗事,不能有一兩件可笑可嘲可詈可罵之事彼此打趣,友誼恐怕也會變得空洞吧?
有時獨坐細味「瑕」字,也覺悠然意遠,瑕字左邊是玉旁,是先有玉才有瑕的啊!正如先有美人而後才有「美人痣」。先有英雄,而後有悲劇英雄的缺陷性格(tragic flew)。缺憾必須依附於完美,獨存的缺憾豈有美麗可言,天殘地闕,是因為天地都如此美好,才容得修地補天的改造的塗痕。一個「壞孩子」之所以可愛,不也正因為他在撒嬌撒賴蠻不講理之外有屬於一個孩童近乎神明的純潔了直嗎?
瑕字的右邊有赤紅色的意思,瑕的解釋是「玉小赤」,我也喜歡瑕字的聲音,自有一種坦然的不遮不掩的亮烈。
完七、唯一
八、活
佩玉的人總相信玉是活的,他們說:
「玉要戴,戴戴就活起來了哩!」
這樣的話是真的嗎?抑或只是傳說臆想?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一塊玉戴活,這是需要時間才能證明的事,也許幾十年的肌膚相親,真可以使玉重新有血脈和呼吸。但如果奇蹟是可祈求的,我願意首先活過來的是我,我的清潔質地,我的緻密堅實,我的瑩秀溫潤,我的斐然紋理,我的清聲遠揚,如果玉可以因人的佩戴而復活,也讓人因佩玉而復活吧,讓每一時每一刻的我瑩彩曖曖,如冬日清晨的半窗陽光。
九、石器時代的懷古
把人和玉,玉和人交織成一的神話是《紅樓夢》,它也叫《石頭記》,在補天的石頭群裏,主角是那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外多出的一塊,天長日久,竟成了通靈寶玉,注定要來人間歷經一場情劫。
他的對方則是那似曾相識的絳珠仙草。
那玉,是男子的象徵,是對於整個石器時代的懷古。那草,是女子的表記,是對榛榛莽莽洪荒森林的思憶。
靜安先生釋《紅樓夢》中的玉,說「玉」即「欲」,大約也不算錯吧?《紅樓夢》中含玉字的名字總有其不凡的主人,像寶玉、黛玉、妙玉、紅玉,都各自有他們不同的人生欲求。只是那欲似乎可以解作英文裏的want,是一種不安,一種需索,是不知所從出的纏綿,是最快樂之時的淒涼,最完滿之際的缺憾,是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的惴惴,是想挽住整個春光留下所有桃花的貪心,是大澈大悟與大棧戀之間的擺盪。
神話世界每是既富麗而又高寒的,所以神話人物總要找一件道具或伴擋相從,設若龍不吐珠,嫦娥沒有玉兔,李聃失了青牛,果老走了肯讓人倒騎的驢或是麻姑少了仙桃,孫悟空繳回金箍棒,那神話人物真不知如何施展身手了──賈寶玉如果沒有那塊玉,也只能做美國童話《綠野仙蹤》裏的「無心人」奧迪斯。
「人非木石,孰能無情」,說這話的人只看到事情的表相,木石世界的深情又豈是我們凡人所能盡知的。
十、玉樓
如果你想知道鑽石,世上有寶石學校可讀,有證書可以證明你的鑑定力。但如果你想知道玉,且安安靜靜的做自己,並且從膚髮的溫潤、關節的玲瓏、眼目的瑩澈、意志的凝聚、言笑的清朗中去認知玉吧!玉即是我,所謂文明其實亦即由石入玉的歷程,亦即由血肉之軀成為「人」的史頁。
道家以目為「銀海」,以肩為玉樓,想來仙家玉樓連雲,也不及人間一肩可擔道義的肩胛骨為貴吧?愛玉之極,恐怕也只是返身自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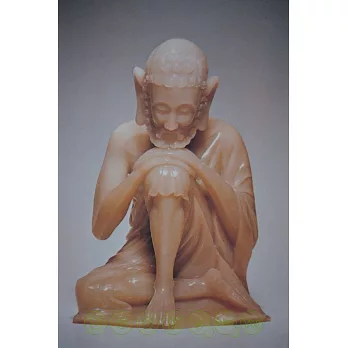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